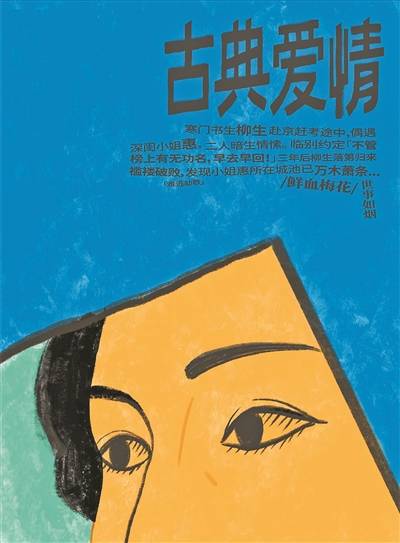
◎贾力苈
近日,孟京辉导演的小剧场新作《古典爱情》在蜂巢剧场上演。这是继《活着》《第七天》之后,他第三次将余华的小说搬上舞台。此次,他将《古典爱情》《鲜血梅花》两部共计三万余字的小说,改编成约两小时的戏剧作品。舞台上白色的迷宫设计、演员夸张的造型、重复机械化的身体动作和台词,以及看似无意义的大段串场表演,延续着“孟氏戏剧”的特点与套路。
孟氏改编往往遇强则强
在当下戏剧发展的语境中,《古典爱情》在舞台上呈现的风格已很难用20世纪90年代的“先锋”“实验”概念定义。但当演出以不断打破观众预期的方式推进,当舞台上人物抽象的行为与荒诞的处境频频引发观众笑声,我们会发现一种在刻意营造的场景间流露出的戏谑和想象力,更有一种戏剧对当下的捕捉与回应。
在《古典爱情》《鲜血梅花》发表的同一时期,正在中央戏剧学院攻读研究生的孟京辉,在宿舍里与朋友争论搞先锋戏剧是否值得,有无未来。他们得出的结论是:要搞戏剧,要改变戏剧。后来,孟京辉筹划排演了那部诗意又残酷的《等待戈多》。再后来,孟京辉成为实验戏剧的前卫代表,20世纪90年代后期,“孟氏戏剧”因其拼贴、戏仿等叙述策略,追求视听层面的快感等可辨识风格,成为戏剧领域的专属名词。
同时,这也是一个饱受争议的词汇。有人质疑其因商业诉求而在艺术上有所妥协,甚至走向媚俗;有人批评其戏剧实验流于形式拼接,故作高深。然而就作品而言,有两点不可否认:其一,孟京辉的戏剧创作始终对青年受众保持着独特的吸引力;其二,在他的创作中,改编占据重要地位,且以改编为基础的作品往往“遇强则强”,越是借助经典文本,越能释放出独特的叙事风格与美学张力。
解构之下保留善意温暖
《古典爱情》是对中国传统才子佳人故事的解构。柳生在赶考途中与惠小姐相遇,他谨遵惠小姐“不管榜上有无功名,都请早去早回”的嘱托,落榜归来时却遍寻惠小姐不见。此后,柳生接连三年科举不中,途中景观一变再变,最终在菜人市场见到已被砍去一条大腿的惠小姐。在惠小姐的哀求下,柳生为其赎身并结束了她的生命。又过几年,柳生再次见到惠小姐,忍不住开棺确认,而惠小姐本将复生,却“只因被公子发现,此事不成了”。
舞台上的《古典爱情》,没有了原作小说俯视全局的视角,演员以近乎独白的方式讲述经历,宣泄情感。柳生三次赶考的情节被前置,循环往复的叙述,搭配着演员单腿跪地又弹起的机械肢体动作,放大了柳生处境的荒诞,惠小姐的吟哦之声也变得更加夸张怪诞。舞台叙事在柳生结束惠小姐生命的一刻,戛然切换至《鲜血梅花》。
不到万字的《鲜血梅花》,是对中国传统武侠叙事的颠覆。武侠作为中国成熟且内涵丰富的叙事类型,近年来在视听艺术中不断与新技术融合,叠加类型元素,开拓出新风格。但无论如何革新,一个除暴安良、匡扶正义且具有行动力的主角,始终是武侠故事的核心。
但在《鲜血梅花》中,替父报仇的经典母题,在儿子不断忘记复仇使命与线索的漂泊中消解殆尽。阮海阔遇到胭脂女和黑针大侠,完全出于巧合借二人之手杀死了仇人。舞台上,本就优柔寡断、记忆不佳的阮海阔,变得更加羸弱、气力不足。癫狂的母亲,无力的儿子,荒诞的江湖,却又在日常场景中保留微小的善意、正义与温暖,这让平日里以自嘲解压的年轻观众,在因阮海阔的行为发出笑声的同时,也完成了释放与宣泄。
为观众预留一方栖居地
向来标榜“根本不用考虑观众”的孟京辉,实际上始终都在舞台上预留一方隐秘的栖居地,让观众在荒诞剧情引发的莫名笑声中寻得归属感。去年年底,小红书发布年度关键词“抽象”,成为一种在青年群体中流行、兼具幽默玩闹气息与些许“不走寻常路”特质的文化现象。如今,无论是文旅推介还是农产品销售,宣传文案不乏颠覆观众惯性认知的创意表达,力求引发年轻受众的共鸣与喜爱。
孟京辉的《古典爱情》在拆解与重组原著小说的过程中,在颠覆传统通俗小说的叙事里,找到了传统叙事与先锋表达通往当下的路径。正如舞台上占据大半空间的白色迷宫装置,成为一种具象的比喻,创作者让意义在舞台与观众之间徘徊,完全不做解答,寄希望于在迷宫中穿梭的观众自发生成感受和意义。这是一种剧场的回应,也是一种对戏剧创作的发问:今天的舞台艺术可以为年轻人提供什么?





